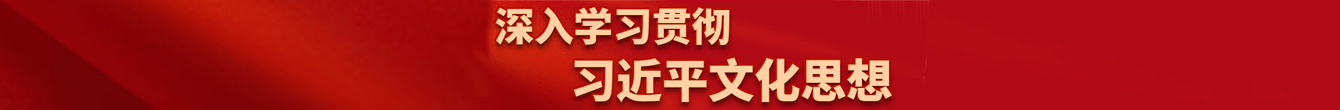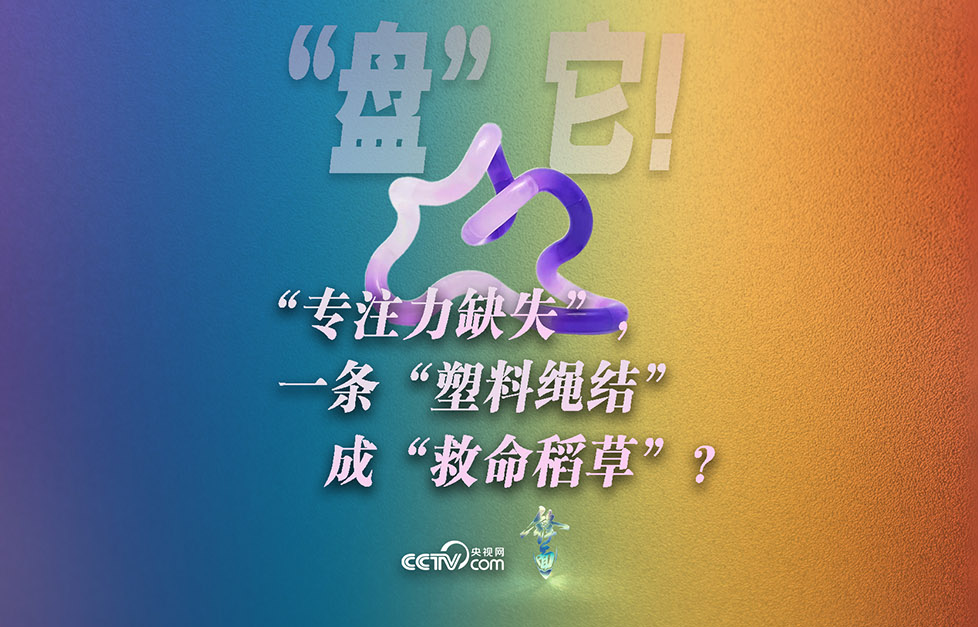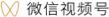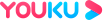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5-07-30 11:21:23
- 来源:中广网
- 作者:钱泓亦 张嘉奕

- 中广网移动端
- 分享到

- 回到顶部
一所“三房一照壁”院落,坐落在丽江古城,登上二楼便可饱览四合五天井的纳西建筑特色,也可一窥非遗东巴舞的风姿。
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院”里,一位纳西族老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东巴舞的发展。其深邃的目光背后,却是非遗传承面临的困境:微薄的个人力量。
这样的困境在大研纳西古乐会和纳西民居博物馆同样存在:古乐会因疫情冲击和老艺术家离世而门庭冷落;纳西民居博物馆则受限于负责人的年龄与资金难以有效地传承和发展。
老人们守护非遗的赤诚令人动容。但仅靠个人力量显然难以实现非遗的长远传承,唯有探索新的保护模式才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
那么,商业化是否能够成为解决资金匮乏人员流失的非遗产业困境的一剂良药呢?

东巴歌舞的“有限商业化”路径
融汇宋元明清建筑风格的天地院,位于四方街50米处的科贡坊,是丽江古城景区着力打造的30个文化院落之一。天地院里的20多名群众演员,身着羊皮坎肩和“披星戴月”服饰的纳西阿爹阿妈成了这里的“台柱子”。
伴随“热美蹉”悠扬的乐声,踏着轻快的舞步,纳西族传统民间歌舞在天地院天天上演。“热美蹉”是纳西族传承千年的集体民族歌舞,这种原生态的舞蹈动作以及发自胸腔的天籁之音,被誉为“原始歌舞活化石”。
负责人和学光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纳西族老人,他曾在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民族文化,在这个行业已深耕二十余年,从编舞到为演员培训,他事事亲力亲为。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游客,紧跟时代潮流,和学光在保留“斩心魔”等东巴舞核心意蕴的前提下,又为东巴舞进行了一些改编,如加快节奏,删除宗教内容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传承,和学光为舞团成员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他表示,以前这里的表演是免费的,但碍于资金匮乏以及到访者减少的原因,他不得不从一年前开始收取演出费用。然而,虽然所收取的费用并不算高,但观看者寥寥无几,维持运营全靠和学光凭着一腔热忱苦苦支撑。
在访谈中,和学光反复提及,当下所采取的商业化收费,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会进一步扩大这种规模:一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已经没有精力在经营模式上进行改革,互联网对他而言也是陌生的领域;二是因为东巴歌舞面临日益严峻的传承断代问题。舞台上的这些舞者大多都已年过半百,少数会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是和学光的学生。维持运营的资金短缺、年轻人非遗传承意愿降低和艺术院校教育体系的缺位,共同导致了人才断代。
离开时,和学光颔首相送,满头银发在深色的纳西古建筑里格外引人注目。“当年,我在搞这个东巴舞协会的时候,头发是黝黑黝黑的;现在,二十多年后,我就成了你们看到的这么一个形象。”和学光说道。
这位老人为了民族文化传承奉献了半生,满头银发俱是他赤子之心的见证。他在资金和传承上的困境,同样也是很多非遗传承人难以言说的无奈。
东巴文的“商业化传播”
很多人对东巴文既好奇又感到疑惑:这种被誉为“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如今是否还在真实使用?使用语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来到丽江后,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东巴文字在古城里随处可见:店铺门匾、墙体对联、文创包装等等,构成一片“符号海洋”。在东巴纸上书写“像是在跳舞”的东巴字,是一份浑然天成的礼物。位于古城光义街现文巷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很好地为游客提供了“写写画画”的深度体验。
集学习、体验、展览和销售于一体的体验馆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巴纸。有写着文字的,灵动活泼的东巴文字衬在古朴的东巴纸上,显得极有韵味;有画着花草鸟兽的,叙述着那些鲜有人知的故事;而书写经书的东巴纸因经常翻阅而呈古铜色,看起来古色古香……每一个象形文字、每一幅东巴画、每一个符号、每一抹色彩,都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变迁与发展,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林里不可或缺的一枝。
体验馆负责人和闰元表示,在东巴文化的核心语境中,书写本身是一种仪式。在他看来,游客的书写体验仅停留在字形的临摹与复制层面,缺乏对语言系统、文字逻辑与背后哲学的理解,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组合书写与文化再创作。

相较而言,真正的东巴文传承人不仅要理解文字,还要理解背后的世界观、宗教观与自然观。“首先要懂得纳西族语言的口头表达,然后是学习单个字的书写,等到熟练掌握之后才有能力去组合使用。”而这些看似简单的流程往往需要“至少三四十年的坚持与积累”。
据了解,东巴文化的学习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传统时期,学习东巴文字只是“上层人士”的特权。而在2003年,东巴古籍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记忆遗产”,这种传统才被打破,东巴文的学习走向了“大众化”的道路。但即使如此,和闰元也强调:“学习东巴文化,首先是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爱好,再看你有没有天赋。这其中也需拜师学艺,经过严格筛选。”
令人意外的是,和闰元对东巴文商品化持开放态度:“文化和艺术,都需要与时俱进。”他指出,只要建立在理解基础上,文创就不仅是市场回应,更是文化传播的方式。“让更多有缘人了解并喜爱东巴文化,就是最好的传承。”
纳西古乐的沉浸式“商业化探索”
如果说东巴文是写在纸上的文化,那么纳西古乐就是响在空气中的记忆。
据了解,纳西古乐由洞经音乐、皇经音乐和白沙细乐三大体系构成,因其融入了道教法事音乐、儒教典礼音乐,甚至唐宋元时期的音乐元素,被誉为“音乐活化石”。
走进大研纳西古乐会,墙上宣科先生与古乐表演团在各国展演交流的照片似乎在诉说这支乐队曾经的辉煌。这支全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乐团,乐师们既没上过音乐学院,演出时也没有乐谱。近千年来,靠着一代代师徒口耳相传,纳西古乐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
店里的古乐器制作者说:“以前演出时,二楼都围满了人。”如今,表演舞台仍保留着传统布局,但在舞台之外,二楼空间已经变成了书店和咖啡馆。
多年前,大研纳西古乐会曾是丽江古城最负盛名的文化地标之一,是丽江旅游的必体验项目。每晚8点,这里座无虚席,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既被曲子老、乐器老、演奏者老的“三老”魅力所吸引,也被宣科妙语连珠的中英文主持风格所折服,场场爆满的纳西古乐会成为丽江最闪亮的文化名片。
如今,古乐会的盛况已不复当年,演出厅内常常只有寥寥数人,甚至观众席上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奏者还少。但古乐会仍然坚持每天演出,哪怕只有一名观众也要奏响千年古调。
但纳西古乐会却在宣科离世后出现“IP断层”。古乐会主理人宣智莲坦言:“父亲将民间乐班打造成了文化IP,但过度依赖个人影响力让古乐会面临了挑战。”

从英国留学回来后的宣智莲,在大研纳西古乐会的楼上增加了宣科书房。这个文化空间既延续了纳西院落的结构,又融入了时尚简约的设计。一楼陈列的纳西古乐的珍贵乐器、演出道具与老照片维系着与过去的血脉联系;二楼的图书馆除家庭藏书外,还有地方文献、东巴古籍等。
然而,这种模式带来的收益却微乎其微:二楼的咖啡馆环境清雅,香囊体验店创意十足,书店媲美一众网红店,却鲜有客人光顾。
“非遗+商业”本可以成为一副好牌,为何发挥不出其真正的效用?宣智莲有她的担忧,过度商业化有可能破坏非遗的精神内核,所以当前营销策略较为保守。“从技艺传承转向更广阔的文化思想传播,才能让纳西古乐从旅游消费品回归到其作为生活智慧与精神遗产的本质。”
其实,商业化并非洪水猛兽,它可以为非遗提供可持续的土壤,关键就在于如何守住文化的根。大研纳西古乐会从单一的表演场所升级为沉浸式文化空间,是宣智莲用一种全新的、更稳定的方式来延续宣科非遗传承事业的尝试。
非遗的未来,或许就在这些不断探索与选择之间慢慢清晰。
- 免责信息:本网站没有经营性质和盈利属性。本网站摘录或转载的属于第三方的信息,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转载信息版权属于原媒体及作者。 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擅自转载使用,请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有本网转载且涉及到版权问题的,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