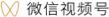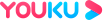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5-10-06 10:11:06
- 来源:中广网
- 作者:宋伯胜

- 中广网移动端
- 分享到

- 回到顶部
秋天的栾树

因为好看、长得乖才引起我注意的。
我,老头子。好色而不贪色,也没有贪的能力。
我说的是树,它叫栾树。
入秋,薄凉。坐在楼顶阳台上无目地的四处张望。茫然、无语、痴坐是退休生活的常态。
从楼顶上看对面的山隔半座城,城的一半挡住了山的一半。远看,那山就像城的一顶帽子。
山的绿色呈曲线逶迤,偶尔起雾,雾夹在绿色的林子里,像纱巾,帽子上扎了一朵蝴蝶结。这时的栾树混在其它杂树中间,无任何特色可言。到了秋分,其它杂树还是绿色,唯有那片′栾树重重叠叠。先由绿色变黄色,再由黄色变成紫红色。那山,也因栾树一簇多了线条的风韵,多了色彩温馨,多了秋天的成熟。
栾树是因为多情才不安份的。

据史料记载:栾树生于古时"士大夫"的墓地,因种子漆黑溜圆像鬼的眼晴,被称为"鬼树″。或许是时代变了,鬼树没有市场;或许是"士大夫"改了称谓,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又或许是好事者移花接木,不懂风水…….总之,栾树来到城市这是事实。我相信,城市绝对不是它的墓地。
入秋后,楼顶对面的那座山不断的变幻颜色。因没有近距离观察,我只能说:"栾树花一开,那山就像一幅油画"。
其实,我经常散步的澧水河边也有栾树,只因规模引不起视觉冲击而被忽视。现散步之余多了心机,目睹栾树开花之过程,也可举一反三,为时不晚。
栾树属落叶乔木,高大挺拨,开花时老树枝与新枝条颜色各一,反差过大,不像是一蔸长树出来的。新枝条嫩嫩的、一蔟簇的,像海底觅食的鱆魚张牙舞爪。
栾树开花前的枝条又像穗状谷粒,开花后的绿色袍衣变成花蒂,花是米黄色,像袖珍小野菊。约一星期后,菊花落地,结出无数由三片叶子合抱的紫红灯笼。这时,枝条负重但不弯腰,微风吹拂,整个身子都在枝条上摇晃,这是栾树特有的舞蹈。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一文中是这样描写的:"那儿有几颗大栾树,秋季开出一簇簇细而稠密的小黄花,花落了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变黄,成熟了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不免检了一个还要检一个"。
受史铁生短文的启发,老头子在阳台上痴坐,不等于没有想法。我是这样想的:栾树从墓地来到城市不是扮鬼的,它鬼一样的存在因为美的存在。这种美,正是城市里普遍缺失去的一一人性之美!
- 免责信息:本网站没有经营性质和盈利属性。本网站摘录或转载的属于第三方的信息,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转载信息版权属于原媒体及作者。 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擅自转载使用,请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有本网转载且涉及到版权问题的,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