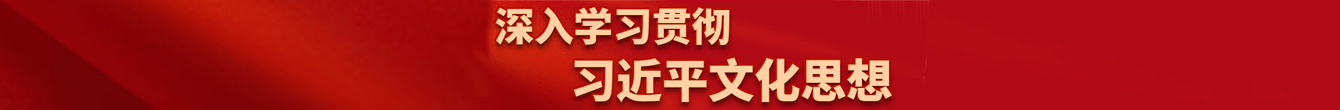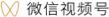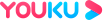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5-11-05 13:22:48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中广网移动端
- 分享到

- 回到顶部
|
位于印度尼西亚万隆的亚非团结纪念碑。 |
|
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内景。 |
|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主会场外景。 |
|
世贸组织第十二届“中国项目”圆桌会高层论坛现场。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工作人员向参加“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主题边会的嘉宾介绍情况。 |
|
位于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外景。 |
联合国成立80年来,搭建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主权独立和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南方国家也为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本期特邀5位国际法领域专家,就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法治的贡献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完善国际法治进行探讨。
郑若骅(国际调解院秘书长、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席主席)
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学院院长)
司芙兰(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南非大学国际法荣誉教授、南非国际问题专家)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创立后,国际法体系经历了从少数国家主导到多元共治的深刻变革
郑若骅: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世界总体保持和平、实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国际法体系经历了从少数国家主导到多元共治的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通过集体行动和创新实践,发展中国家推动了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发展,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通过了体现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十项原则。会议后,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成立,积极参与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框架,进一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立法能力。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发展中国家作为集体力量参与国际立法,源自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亚非拉等地区国家积极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参与国际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强调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自决权,并要求殖民统治立即结束。1986年生效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与发展权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既负有人权保护义务,也应促进集体发展。这拓展了国际人权法的范畴,体现发展中国家在丰富人权理念上的贡献。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承担气候变化治理的责任时分工更加公正合理。
柳华文: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二战后国际法的量变与质变,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通过集体行动将主权平等、安全、发展等诉求转化为国际法体系中的内容。1974年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提出主权平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等原则,主张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表明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为完善国际秩序而展开行动。历时9年谈判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立法、实现制度创新的典范,公约中出现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等内容,都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制定上的创新与话语权的提升。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了全球各种力量的平衡,然而大部分国际法的基础构建于数十年前,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面临困境。设计新的国际法框架和内容十分必要,这需要人们对当前的困境进行反思,并以符合当下形势的理念作为指导。地缘政治、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合作发展,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法律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强大武器。中国始终致力于以法律维护自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主张各国超越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对国际法的创新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与塑造“发展中国家国际法”,使其更具特色、吸引力和影响力
郑若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促进和塑造“发展中国家国际法”,使其更具特色、吸引力和影响力。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发展和贡献。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化解矛盾的示范。今年,中国会同30余个国家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这一由发展中国家引领的争端解决制度创新,弥补了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局限性,吸引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关注。
司芙兰: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提出并推进了一系列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倡议和决议,积极承担创新国际法体系的责任。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获得通过,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人权问题,契合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公平、包容的人权治理的期待。中国推动通过此类决议,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还通过提供法律援助、培训法律人才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参与和牵头的一系列新型国际组织或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它们寻求实现全球力量的再平衡,推动国际规则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和共同利益。中国提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推动相关国家跨境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呼应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权”概念。中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发展促人权决议,呼吁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消除发展的障碍,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法领域的规则制定与解释,展现出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塑造公平、包容、可持续国际规则体系的努力。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与联合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等原则高度契合,“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获得各国积极响应,不断转化为国际共识。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国既坚持遵守规则,又强调公平适用,不仅运用世贸组织法律条款维护自身权益,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策略与经验,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解读方面的能力建设。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重要缔约方,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与资金、技术义务,确保全球气候法体系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脱贫需求。这不仅使“气候正义”成为国际法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权益。
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确保国际法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工具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尽管发展中国家有诸多创新和贡献,但国际法仍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国际规则制定和解释权长期被少数西方大国垄断,发展中国家代表比例偏低,导致判决的多元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在具体的国际诉讼与谈判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加强团结,增强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并通过机制对话、平台建设和集体行动,推动形成更加包容、公平的国际法律秩序,确保国际法真正成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工具。
全球科技公司正处在快速扩张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本国数据主权、数据安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等最新科技领域,中国政府出台管理措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中方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的诉求相契合。2024年,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国参加决议联署;202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声明》。这些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该领域达成的最新共识。
司芙兰:中国参与的多个多边合作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有效框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明确提出,支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拉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都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纳入发展进程,在促进国际法进步、为国际法治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以主权平等、提升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为核心,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示范。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中国在长期参与多边机制中形成了兼具务实性与战略性的法治路径:既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又通过积极参与谈判、提出倡议、解释规则,推动国际体系更具包容性与公平性。在法律能力建设方面,非洲国家希望中国扩大法律人才培训,帮助非洲国家在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中增强专业能力。在数字贸易、气候治理、知识产权与全球公共卫生等新兴议题上,非洲国家期盼中国在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新规则不会重现“南北不平等”现象。
柳华文: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应积极推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丰富与发展,充实现有争端解决途径。在网络空间、外空、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方面,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加强技术层面的研究、发展与实践,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形成。中国可以会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国际法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打破西方在国际法理论和话语体系上的长期垄断,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构建一套能够反映自身立场和价值观的国际法话语,进一步形成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法”的理念和体系。
从在万隆会议上播下种子,到在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茁壮成长,全球南方国家已经证明,它们是推动国际法朝着更公平、更正义、更包容方向发展的关键力量。未来的国际法治秩序,必将深深烙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印记。
(本报记者张博岚、王骁波、谢亚宏、戴楷然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5年11月05日 17 版)
- 免责信息:本网站没有经营性质和盈利属性。本网站摘录或转载的属于第三方的信息,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转载信息版权属于原媒体及作者。 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擅自转载使用,请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有本网转载且涉及到版权问题的,请联系删除。